导语:
修改发表于2025年07月02号 19点 阅读 7228 评论0 点赞26 ©著作权归作者所有
5月份以来老小孩读书会组织了《燕东园左邻右舍》读书活动。我很喜欢老建筑,也非常关注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故事。徐泓教授的这本书把二者完美的结合,我读来很配胃口,受益匪浅。
一本书,一座园,一群人,一段穿越时空的共鸣。7月2日下午,老小孩读书会举办了共赴一场文学与记忆的云端之约。《燕东园左邻右舍》作者徐泓教授做客直播间,与老小孩一起分享书里书外的故事,重温那些让无数读者泪目又暖心的燕东往事。以书为媒,共赴一场跨越年龄与时空的对话。在文字中相遇,在记忆里重逢。我虽然听力不好,但还是戴着助听器,参加了这个难得的见面会。
徐 泓,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,1998 年前从事新闻工作,高级记者,曾任中国新闻社新闻部副主任,北京分社社长。徐教授出生在燕东园,父母亲都是北大教授。作者亲述燕东园的“人”与“情”。徐泓教授带我们走进燕东园的四季晨昏,细数书中未尽的细节:从大师邻里的烟火日常,到时代洪流中的坚守与温情,感受历史夹缝中的人性光辉。
互动问答,与作者“面对面”,了解徐教授关于创作、关于燕东园、关于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任何问题,直播间弹幕见!
为什么这本书让老小孩感动?《燕东园左邻右舍》以会说话的老建筑为引子,用温润笔触勾勒北大燕东园的知识分子群像,既有学术泰斗的赤子之心,也有市井百姓的柴米油盐。老小孩读书会首期共读时,书友们纷纷感慨:记忆需要被传递,历史不该被遗忘。无论您是《燕东园左邻右舍》的读者,还是热爱文学、关注历史的长者,都能带着故事来,带着思考走,都可以在徐泓教授的讲述中,重拾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记忆碎片。
在中国现当代史上,周培源、钱玄同、朱光潜、冯友兰、季羡林、费孝通、王力、冯定、翦伯赞、梁漱溟、冯至、何其芳、陈梦家、金岳霖、于敏、徐献瑜、陈占元、岑麒祥……是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,而他们都曾住在同一个地方,那就是别名“东大地”的燕东园。燕东园在北大东门附近,前身是明清时期的成府,据说在乾隆年间为太监营房,老太监们从宫里出来,死后就葬于此地。20世纪20年代,时任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买下这77亩地,建成了如今的燕东园。从此,一代代知识人与这里产生交集。
燕东园堪称一片“学术沃土”,曾聚集了北京大学文、史、哲、语言、政经、数理化等多个学科的顶尖学者。他们在这里教书育人、著书立说、度过或辉煌或坎坷的岁月,使燕东园成为了北大乃至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人文地标。
从20世纪20年代起,燕东园囊括了一批批杰出学人,但20世纪是革命与巨变的年代,知识分子也无法独善其身,他们的学识令人钦佩,他们在后半生不同的境遇,更令人唏嘘。
因此,燕东园是一个重要的坐标。但长期以来,缺乏一部专门挖掘其文化价值的专著,直到徐泓填补了这一空缺。打开此书,既能发现王世襄的乐园、何其芳的读书会,也能看到冯至和杨晦“一个甲子的友谊”、周一良对于陈寅恪的愧疚,还有不能忘却的陈梦家与赵萝蕤。徐泓以扎实的笔触,书写了一部知识分子精神史,也抢救了一段不该被遗忘的过去。
他们大多学贯中西,在各自领域造诣深厚。即便在特殊年代,仍保持着对学术的纯粹热爱,如书中描写的教授们在简陋环境中坚持读书研究,展现出知识分子的学术定力。作品真实呈现了他们在时代巨变中的生存状态:既有对理想的坚持,也面临现实的困境。通过邻里间的日常交往,折射出知识分子群体在特殊时期的生存智慧。通过微观视角呈现宏观历史,在日常叙事中展现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度,对特殊年代的知识分子生存状态进行了人性化记录。
书中人物不是脸谱化的“知识分子”符号,而是有血有肉的个体,他们的喜怒哀乐、困惑坚持都跃然纸上,为理解那个时代提供了鲜活注脚。这种对知识分子群体的细腻刻画,在当代文学中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。
这是一部知识人的精神图谱,也是以小见大、关于一段崎岖年代的痛史。它不应该被遗忘。在北京大学燕东园斑驳的砖墙上,爬山虎正以每年固定的节奏舒展着枝叶。这座建成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教授住宅区,其灰瓦红墙间至今仍流淌着一种特殊的气息——那是钢笔尖划过稿纸的沙沙声,是书架间尘埃在阳光下起舞的微光,是老式台灯下思想碰撞的火花。这里的每一块地砖、每一扇木窗都在无声地讲述着一段段被时光浸染的往事,而那些曾经在此居住的老一代知识分子,则如同建筑本身,在岁月的冲刷中愈发显现出其精神质地。
燕东园的建筑布局本身就是一部立体的知识分子交往史。每栋住宅之间不过数步之遥,却形成了独特的"学术共同体"空间。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曾回忆,他与季羡林先生住所仅隔一道矮墙,“夜半常闻诵经声,晨起必见译稿新”。这种物理距离的接近,催生了思想的频繁碰撞。住宅区的中心花园曾是周末学术沙龙的固定场所,哲学家冯友兰常在此处与学生们围坐论道,斑驳的石桌面上至今留有粉笔划过的痕迹。
住宅内部的空间分配也反映了知识分子的生活哲学。书房永远是最宽敞明亮的房间,书架从地板直抵天花板,中间仅留一人通过的通道。物理学家王竹溪的书房里,黑板占据了整面墙,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公式推导,有些甚至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。这些空间安排不是偶然,而是知识分子将生活场所转化为思想实验室的自觉选择。
在燕东园的老房子里,每一件日常用品都可能承载着特殊的文化记忆。季羡林故居保留着的那台老式打字机,键盘上的字母已经磨损得几乎难以辨认,却曾打出过《罗摩衍那》的优美译文。据家人回忆,季先生习惯在深夜写作,打字机的声响常常持续到凌晨三点。这台机器不仅是工具,更成为了学术坚持的物证。
在物理学家饶毓泰的住宅里,那张磨损严重的书桌抽屉中至今保存着他的备课笔记。泛黄的纸页上,复杂的公式旁总能看到几句用铅笔写下的生活感悟,展现出科学家感性的一面。这些看似普通的物品,实则是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物质载体,它们将抽象的思想转化为可触摸的历史存在。
燕东园的建筑见证了中国现代学术传统的形成过程。在某栋住宅的阁楼里,至今保存着王力先生编纂《古代汉语》时的手稿,密密麻麻的批注显示出学者对学术完美的追求。这些手稿不仅是学术成果,更是一种治学态度的传承。年轻一代学者常来这里“朝圣”,感受老一辈学人严谨的学术作风。
建筑之间的邻里关系也塑造了独特的学术生态。据社会学教授费孝通回忆,他与同事们常常在下班后互相串门,在客厅的沙发上进行“非正式学术讨论”。这种宽松自由的交流环境催生了许多跨学科的思想火花。如今,虽然当年的学者大多已经作古,但他们留下的学术传统仍在燕东园的砖瓦间延续。
读着《燕东园左邻右舍》仿佛能听见历史与现实的对话。这些建筑不仅是物理空间,更是承载着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记忆的文化场域。在这里,每一块砖石都记录着思想的重量,每一片瓦当都镌刻着学术的坚守。当新一代学子走过这些老建筑时,他们触摸到的不仅是冰冷的建筑材料,更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度。这种精神将通过建筑的永恒存在,继续滋养着未来的学术生命。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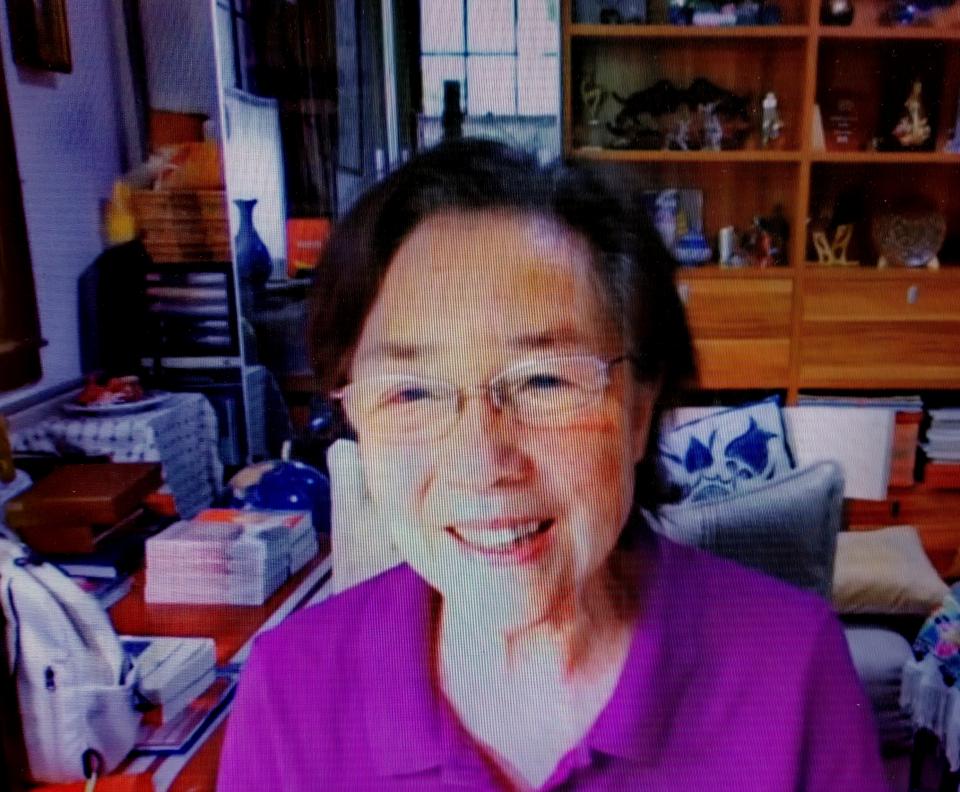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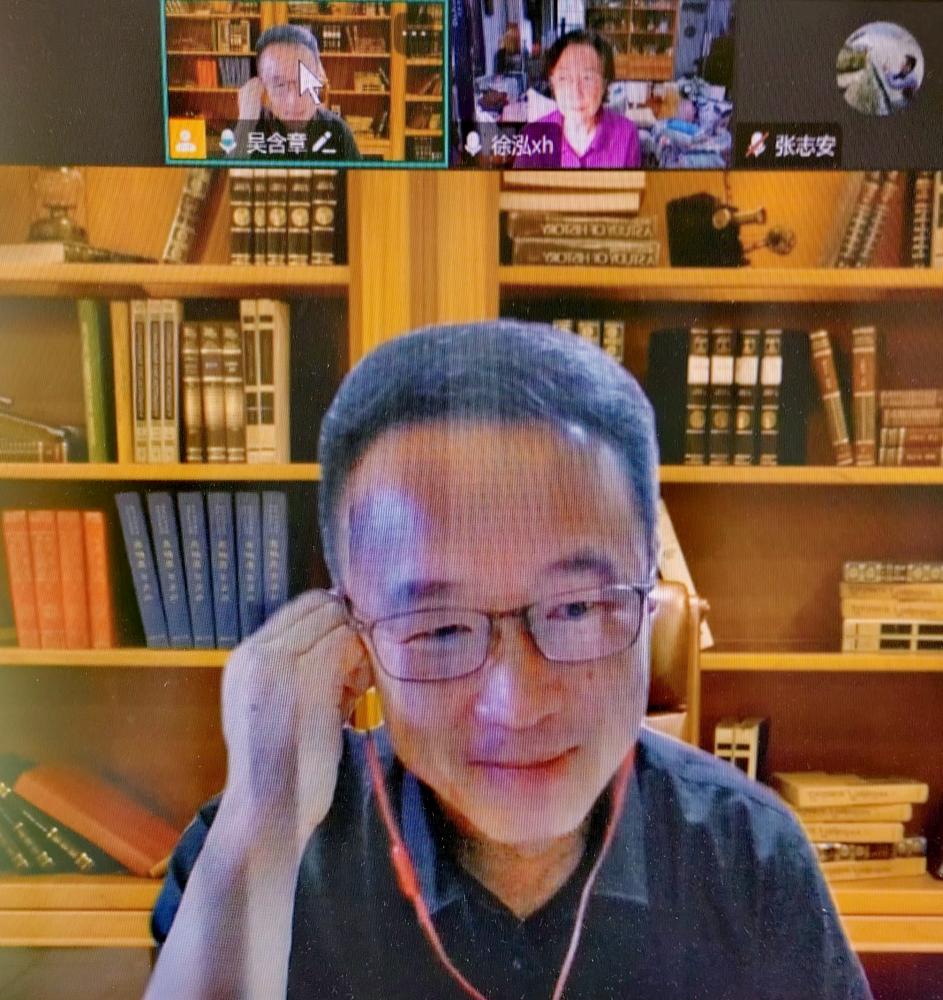
信纸作者:茹歌
请选择你想添加的收藏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