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原创】追寻中医药文化四十年间
追寻中医药文化四十年间
叶子
2002年末《新民晚报》刊登了这样一篇报导:上海历史博物馆收到了一批珍贵的捐赠品,这批乍看并不起眼的“老古董”却是蔡同德药业有限公司的置业家当,见证了一段上海工商业的历史年轮和中药业的发展轨迹。……博物馆有关人员说,这批捐赠品对于上海地方史、中医药行业史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。同时,我也发表了《那一台脚踩的印刷机》文章,讲述了在这批捐赠品中的一部印刷中药方单的脚踏印刷机。

这台老式印刷机是中国工业革命后,上海制造的第一代铅字印刷机,还是当年徐重道开设印刷厂时留在总店(北京西路101号,文革中改名向明中药店,现因市政动迁已撤网)的一台。我担任办公室主任时,公司里还在用老式的铅字打字机,通过油印纸只能印制五号宋体一种字体,要印大字或其他字体,就得靠那台印刷机了。为了印制文件材料需要,我多次到过印刷房。印刷前先要排版,根据要求选用不同的字体、字号的铅字,然后才能开始印刷,用脚一踩就印出一份初稿,通过认真校对后,脚下“咔咔”响,印张份份来。别看这台印刷机这么“老爷”,解放前还为中药行业共产党外围组织益友社印过革命传单,与当时的黄色工会对着干呢。
到了九十年代,办公室丢弃了铅字打字机,从四通电子打字机进入到电脑时代,字体越来越多,字号也越来越全,不仅能用电脑排版,还能打印出各种彩色图片,印刷的老师傅退休后,更没人去摆弄那台印刷机了。活字印刷术是我国北宋庆历年间(1041~1048)的毕升创造的,从泥活字、木活字、铜活字、磁活字、锡活字到铅活字,时代在发展,印刷技术也在不断提高。这台闲置的老式印刷机终于被请进了上海博物馆的大门,成为上海中药发展史上的一个见证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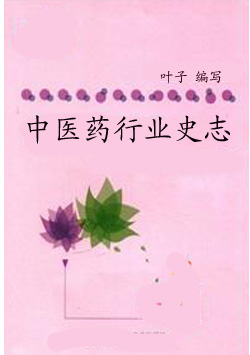
七十五年人生,七十五年中医药情结,我关注中医药发展,关注中医药传统文化。在漫长的华夏文明发展过程中,从神农尝百草至今,中医药行业印刻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。我是中医药人,也是中医药历史文化工作者,我的志向就是继承前辈中药人的遗愿,追寻中医药文化的根,传承中医药的传统。1999年,蔡同德药业有限公司清除了贪污受贿的群蛀案,调整了党政班子,尤其是在新建立的新世界集团有限公司领导下,蔡同德药业重新走上了正规,在改革开放中迈向新世纪。从而,也激励我在新世界集团建团十年间,努力追寻中医药文化。
中医药是我国数千年来,通过劳动人民向疾病作斗争所积累起来的宝贵文化遗产,是中华民族的骄傲,值得重视和巩固,并让它发扬光大,不断发展。然而在中医药近代史上却发生了多次抵毁中药,企图取消中药的事件。旧社会,一些人却对祖国的文化遗产——中医药不关心不爱护,还屡次加以摧残破坏。清朝官僚褚民谊、朱家骅极力贬低国药,对中医中药横加歧视排斥,并说“中医中药是不科学的旧医旧药”,主张“取谛”中医中药,要把这份宝贵的民族遗产从根本上进行废除和扼杀。1925年冬,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教育部总长汪伯唐,也公开提出废除中医中药,把祖国的中医药遗产说成是“伪科学”,当即受医药联合会等有关团体的强烈抗议。1929年国民党政府时的卫生署部委员余岩,提出废止中医中药的议案,当时就引起了医药界人士的强烈抗议。新中国成立七十五年,时有人提出要取消中医中药,并声称“中医药是巫医继承下来的,从来没有科学依据”,是“穿着长袍马褂,带着花镜,留着辫子,陈年的历史垃圾”。

数千年的历史史实,证明中医药与每一个中国人息息相关,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,是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,关键是我们对中医药还不够重视,对中医药的现代化还不够关心,尤其对中医药历史文化的追寻更少关注。中药方剂中讲究君臣佐使的配伍体系,不仅符合科学理论,还是具有丰富的哲理;张仲景《金匮要略》中的薯蓣丸方,从而宫延秘方流传到民间,发展成为同仁堂的牛黄清心方,处方中增加入了牛黄、人参,去掉了重金属和砷砂,使之成为名牌中成药;还有李时珍历经艰险,亲身考察中草药,收集民间秘方,写出了举世瞩目的《本草纲目》;这不只是一个传奇、一则典故、一段故事,而是展现了丰富的中医药文化。
蔡同德堂的“治病在前,救人是本”的宗旨、“崇德济世,弘古扬今”的理念和“同效歧黄求良药,德存本草寄诚心”、“同心为本草,德仁造民福”、“同舟但愿求医少,德心不虑药尘多”等的楹联是中药文化;胡庆余堂的“戒欺”、“真不二价”的经营箴言和“采办务真”、“修制务精”的经营作风是中医药文化;童涵春堂国药号的“两淡三制”、“童薄片”和“浸(药)煎(汤)榨(汁)化(膏)滤(渣)熬(炼)收(取)”的熬膏七字诀是中医药文化;群力草药店“群力群力,济世为人”的理念、“群力采集中草药,力图妙手济世人”的精神是中药文化;还有蔡同德堂的“鹿鹤寿星”商标、胡庆余堂“雪记”商标、群力草药店的“小草”商标,童涵春堂的“涵”字商标,也都是中医药文化。弘扬中医药文化,需要我们中医药人的不断努力,在浩瀚历史大潮中发掘被太多灰尘所掩埋的真谛。

2006年我重回总公司,拾起停笔多年的中医药史志工作,为了寻觅一段上海中药历史发展的轨迹,传承中药文化,我又一次来到了上海历史博物馆。从1991年3月捐献的长算盘(系蔡同德药业有限公司前身黄浦区药材公司捐献的,长达四米,宽二十七厘米,共有一百四十九档,目前公司还保存着一对长算盘),到2002年那批的“老古董”,我再一次感受到中医药文化的魅力。为了中医药行业发展的轨迹,我不辞辛劳地奔走在档案局、图书馆,寻觅历史的资料,一次又一次地走访中医药老职工,收集着中医药的传闻轶事,迎着晨曦出门,伴着星月回家,积累了大量的资料,为我参加编纂中药史志打下了丰实的基础,也为我在医药报刊上发表中药史志文章提供了丰富的素材。
中医药文化涉及面广,内容丰富,不仅每一味药材有着引人入胜的来历,跌宕起伏的故事,每一家老号字有着荣辱兴衰的传奇,波澜壮阔的历史,就是中药店的百眼橱、青花瓶、切药刀、铁船、铜舂都传承着中药文化。中医药讲究五行八卦,金克木、木克土、土克水、水克火、火克金。不同的药材有着不同的药性,不同的药材就需要用不同材质的中药工具来制作。捣药用的捣钵常有铜制的铜舂,是一个罐状的母体,一根铜杵,捣药时还有一个铜盖防止碎末溅出。我还见过石制和瓷制的捣钵。石头制做的捣钵比较大,可用来捣碎较大、较硬的药材,用捣钵捣的药主要是石膏、紫石英、白石英等一些矿物质;脚踩轮柄,用铁船碾药更是中药行业的一个特色,既要掌握高超的加工技能,又要熟悉中药的性味;还有竹制的药筛,按筛孔的大小严格分为九个号,一号孔最大,九号孔最小,根据不同的药粉选择不同号的药筛进行筛选。如今中药加工采用机器,这些中药老家伙也渐渐地淡出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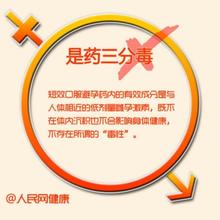
“天地之间有杆称,那称铊就是老百姓”,中药店一杆小小戥子,称中药饮片的小称,同样也有着深厚的文化素质。戥子是专门称量金银和贵重药品的精密衡器。据传公元前221年,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后就有了称的雏形,到了东汉初年木杆的称应运而生,成为后来戥子的前提和基础。到了唐宋时期,我国衡器发展日臻成熟,直到公元1004~1007年之间,我国第一杆戥子诞生了,精细到两、钱,甚至分、厘、毫,其精度在世界衡器发展史上也是罕见的。
中药店里,一般药材都放在镶有锃亮铜拉手的百眼橱格斗里,贵重的药材放在锡盖的青花瓶内,抓药时把中药一味一味地放到小戥子上,配药要准确,称药也要准确,才能保证药的疗效。上辈都是中药人,我从小就熏陶在中药氛围中,中药文化的深邃内涵和厚实底蕴,让我十分痴迷。读书后的空余时,我常会到父亲工作的中药店,看他和叔叔伯伯们脚踏滚轮用铁船碾药,手握刀柄把中药材料切成薄片,拿着铜杆舂药,用铜锅煎药汁或熬药膏,更多的是看他们抓药,拿着病家的药方,按着用毛笔字书写的药名,从百眼橱和青花瓶中为病家抓药,然后用一张印有药店字号的纸张,包成四角方方的虎头包交付病家。百眼橱上没有什么标记,全凭记忆随手抓取所要的中药,更有用小戥子称药让我心仪。右手提戥子,食指和中指轻夹方子,小姆子还要压住称头保持平衡,左手拉抽屉抓药放入称盘,再用大姆指和食指捻动称杆以调节戥砣,还可用左手扶戥子杆,右手用称戥盘抄药,这些都不是笔墨所能描摹的。配药要准确,称药也要准确,这样才能保证药效。我到童涵春堂北号担任党支部书记时,也曾学过抓药称药,一个一个的格斗,一味一味的中药,一次一次的戥称,常常手忙脚乱了好半天。如今虽然退休了,然而拿起家中收藏的那杆铜制的戥子,似乎又站到了百眼橱前,听到拉动格斗的沙沙声,闻到了幽幽的药草香,抚摸着铜杆、铜盘、铜链、铜跎,我更感悟着中医药文化的丰富。

《聊斋志异》的作者蒲松龄,不仅博览群书,还精通医学,他还曾配制过具有祛暑、清热、清痰、通血脉、健心脾、改善睡眠功能的药茶——案饯菊桑茶。正是蒲松龄对中草药的药理、特性、功能的了解、他撰写了一部为中草药作传剧本《草木传》、运用拟人的手法、以草木充当角色,使之人格化,情节化、如老成持重的甘草、勇猛刚毅的大黄、强悍成虐的番木鳖等等,借用药物间性能的生克制化、“十八反”性能、功用、产地、形态、炮制方法等来展开故事。在上海市档案馆查资料时,我认真翻阅过根据《草木传》改编的章回小说《草木春秋》,书里介绍了常用中药五百多种、数百个方剂,通过细致地刻画和描述,让人们在领略文学风采的同时,了解了中药方剂知识。文章寓中医药知识于幽默风趣,中,让我深感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,丰富内涵,深厚底蕴。蒲松龄的不愿“去读而贾”,推倡“贾又不忘文业”,把商业领域作为读书人建功立业之地,从而致力于赋予商人生活以浓郁的诗情画意,更让我感悟到作为中药人更要为中药文化而奉献。
似水年华七十五年。想当年,而立之年的我走进了黄浦区药材公司的大门,如今我已是退休十五年的老中医药人士。我庆幸自己从事了中医药事业,踌躇满志地走进了中医药行业,在这片古朴的土地上耕耘、浇灌、奉献自己的爱和青春年华。在编纂中药史志同时,我还编写了《黄浦中药传闻轶事》(一、二、三),退休后我着手撰写了一部《草木春秋中药篇》,还独立完成了《上海黄浦区中药和中药职工史》等历史文化资料。中医药是祖国的宝贵遗产,同样需要与时俱进,不断用科学的精神加以提升和发展,我愿用有限的年华,为追寻中医药文化发挥余热!
(注:您的设备不支持flash)
信纸作者:叶惠麟笔名叶子
请选择你想添加的收藏夹
- 未定义0条内容 你没有登录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